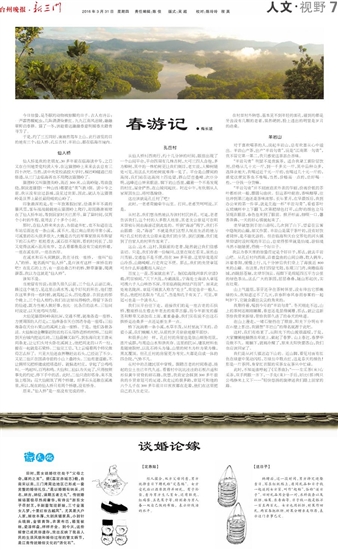今日惊蛰,是冬眠的动物被惊醒的日子。古人有诗云:一声霹雳醒蛇虫,几阵潇潇染紫红。九九江南风送暖,融融翠野启春耕。猫了一冬,该趁着这融融春意明媚春光踏青寻芳了。
于是,约了三五同好,施施然驾车上山。此行游览的目的地有三个:仙人桥、孔丘古村、羊岩山,都在临海市境内。
仙人桥
仙人桥是我的老朋友,30多年前在临海读中专,之后又在台州地委党校读大专,在这猫狸岭上来来去去总有三四十次吧。当然,读中央党校函授大学时,桐岩岭隧道已经修通,从三门去临海再也不用爬这猫狸岭了。
猫狸岭又叫猫狸类岭,高近 300米,山高岭陡,弯曲盘绕,据说连猫狸(一种山兽)都要走“类”(跌)倒。读中专之前,我从没有出过县城,没见过世面,因此,就认为这猫狸岭是世界上最长最险峻的山岭了。
印象最深的是,有一年放寒假回家,恰遇多年不遇的暴风雪,客车战战兢兢地在猫狸岭上爬行,却因路滑被堵在了仙人桥车站,等到回家时天已黑尽。算了算时间,仅两个小时的车程,竟用去了十多个小时。
那时,在仙人桥来来去去,为前途奔忙,竟不知道在这车站后面还有一条山溪。溪不大,是江南山里的寻常小溪,可溪里的石头很多很大,大概是古代的军事家排兵布阵留下的石头吧?粗粗看去,溪石很不规则,看的时间长了,却又觉得这溪石乱而有序,怎么看都像是没有完成的桥墩,一座在溪东岸,一座在西岸。
在溪水和石头间跳跃,我在寻找一座桥,一座叫“仙人”的桥。地名既叫“仙人桥”,是应该有这样一座桥在的吧?在乱石的上方,有一座沧桑古朴的桥,野草萋萋,爬满薜荔,我以为这就是“仙人桥”。
谁知不是。
当地留有传说:在很久很久以前,三个仙人云游江南,路过这个地方,见这里山清水秀,是个好玩的所在,他们想在这里多待一些时候,就驾起云头,四处漫游。在回去的那个晚上,三个仙人相约:我们在这里玩得畅快,得留下各自的仙迹,既为当地人做好事,也比一比各自的法术。三仙同时说定,以天亮鸡叫为限。
大仙见猫狸岭岭高坑深,交通不便,就准备造一座桥,方便周围的人行走;二仙准备在天台国清寺造一座塔;三仙准备在天台石梁山的溪涧上造一座桥。于是,他们各做各活。大仙挥动金鞭驱赶附近的石头用作造桥的材料,二仙则到天台城内挖运灶砖,三仙最懒又取巧,到东海向龙王借来两条龙,让它们头对头卧在溪涧上,他把两龙的口舌一拉,接在一起就是石梁桥。三仙完工后,飞上云端看两个师兄做得怎么样了。只见大仙还在挥鞭赶运石头,已经运了不少。又见二仙正在国清寺前的小山上叠砖头。三仙有意逞能,不让俩师兄把桥建成把塔造好,就躲进村庄,学起了公鸡鸣叫。一鸡起叫,百鸡和鸣。大仙和二仙以为天亮了,只得按照事先的约定,停下手中的活。此时,二仙只造好塔身,来不及装上塔顶;而大仙刚筑了两个桥墩,好多石头还散在溪滩里,所以,现在的仙人桥只有两个桥墩,没有桥身。
原来,“仙人桥”是一座没有完成的桥。
孔丘村
从仙人桥村西南行,约十几分钟的时间,眼前出现了一个山间平台,平台四周有几株古树,大可三四人合抱,多为樟树,其中的一株柏树更让我们侧目,老实说,大樟树随处可见,而这么大的柏树就难得一见了。平台是山腰间的高岗,我们站在这高岗上四处望,群山层峦叠嶂、次序分明,远峰近山皆来眼前。脚下的山岙里,藏着一个不易发现的村庄,屋舍俨然,在山坡间起伏。时近中午,有炊烟从人家屋顶生出,将村落缭绕。
这应该就是孔丘村了吧?
此时,一老者荷锄牵牛而至。打问,老者笑呵呵说,正是。
从村名,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该村村民姓孔。可是,老者告诉我们,这个村的大多数人姓章,其老太公章廷可在明末崇祯年间由海游迁到此处的。听到“海游”两字,我们不由眼睛一亮,“海游”不就是我们这帮人现在生活的地方吗?孔丘村的老太公原来是我们的乡贤。误打误撞,我们竟到了自家人的村里作客来了。
这山、这水、这村,及眼前的老者,陡然就让我们倍感亲切。只是,我们存着一份疑问,这里在现在看来,虽然山川秀丽,交通也不是不便,但在300多年前,这里毕竟是深山冷岙,山路崎岖,行走肯定不便。那么,我们的先贤章廷可为什么弃通衢而入深山?
百度上一查,答案就出来了。据《临海陇洲章氏宗谱》载:明宗祯间,“天下大乱,为避战乱,宁海处士海游人章廷可携六子入山唯恐不深,寻至临海陇洲结庐而居”。原来此处地名陇洲。章廷可被族人称为“处士”,肯定也非一般人。那么,他把村名取为 “孔丘”,当是和孔子有关了。可见,章廷可也是一个读书人。
我们从平台往下走,迎接我们的是一座古老的石拱桥,整座桥丛生着去年老去的荒草古藤,而今年新发的藤茎和野草又添加在上面,重重叠叠,我们实在说不出这石拱桥是沧桑多一点还是新生多一点。
桥下流淌着一条小溪,水草丰茂,从村里流下来的。沿着小溪,我们蜿蜒入村,从前的岁月徐徐地撩开面纱。
和很多山村一样,孔丘村的房屋也是依山顺势而筑,连片成群,与周边山水和谐共存。这里的民居,建筑材料也是随地取材,以乱石砖头为墙,山里的树木为柱为梁为椽,黑瓦覆顶。但孔丘村的房屋更为考究,大都是自成一体的四合院,气势不凡。
在村中的古建民居中穿梭,脚踏古老的村间巷道,扬起的尘土也已年代久远。看着村中坑坑洼洼的石板古道和形似黄牛背脊的卵石路,我想,我肯定会踩到300多年前我的乡贤章廷可的足迹,我走过的很多路,章廷可和他的六个儿子在300多年前日日夜夜都在走着,他们在这里把自己的人生走完。
在村里村外转悠,基本见不到年轻的面孔,碰到的都是牙齿没有几颗的老者,虽然硬朗,脸上透出的明显是岁月的沧桑。
羊岩山
对于喜欢喝茶的人,说起羊岩山,总有欢喜从心中溢出。羊岩山产茶,出产“羊岩勾青”,说是“江南第一勾青”,我不管它第一第二,我只感觉这茶甚合吾味。
“羊岩勾青”明显不是贵族茶,适合我辈工薪阶层饮用,价格从几十元一斤,到一千多元一斤,其中品种众多,选择余地大,我喝过近千元一斤的,也喝过几十元一斤的,感觉这便宜茶也不难喝,当然,价格高一点的,总好喝一些,一分钱一分货嘛。
“羊岩勾青”并不刻意追求外表的华丽,价高价低的茶叶都形状一般,腰圆勾曲状。但这茶叶耐泡,香味醇厚,往往冲到第三泡还是茶味浓郁。长年累月,在早晨饭后,我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,就是先泡一杯“羊岩勾青”,看着茶叶在玻璃杯中上下翻飞,次第把绿色打开,山野的颜色立马呈现在眼前,春色也来到了眼前。掀开杯盖,细啜一口,馨香盈鼻,一天的好心情就起来了。
老早就想到羊岩山游玩,几次到了山下,望着在云雾中隐现的山巅,却又作罢。羊岩山是属于茶叶的,没有好饮者同伴,是不能优游的。但在临海和天台交界处的河头镇里仰望时没时现的羊岩山,总觉得那里就是仙境,游仙境当然不能随便,得挑一个好日子。
我以为春天里的惊蛰肯定是个好日子,那么,就去羊岩山吧。从孔丘村向西南,沿着盘曲的山间公路,数人俩车,沐着春阳,缓慢上行,几十分钟后我们登上了海拔近 800米的山巅。在这里,我们四望无阻,东观三门湾,南瞻临海城,西眺括苍巅,北望华顶云。而脚下是绵延四五平方公里的绿色茶丛,这么广大的茶园,层层叠叠,随山形起伏,实在壮观。
山上气温低,茶芽还孕在茶树怀里,没有伸出它那嫩绿的头,我知道过不了几天,在春阳春风春雨春雾的一起呵护下,它就会露出尖尖的角来的。
我期待着,喝到今年的“羊岩勾青”。冬天刚走不远,山上的茶树还刚刚睡醒,春意还是显得阑珊,那么,就让这新茶给我带来新绿,带给我那久违了的春天的味道。
在山上漫走,一堵石壁挡在了眼前,阳光下分明有羊在石壁上影出,我猜想“羊岩山”的得名就源于此吧。
这时,我们有些累了,而阳光下的山坡很温暖,于是,大家慵懒地躺倒在草坡上,做起了春梦。山上春迟,春梦毕竟做不久。刚躺下,就被冷醒了,原来太阳快要落山,我们也应该回家了。
我们是从河头镇这边下山的。近山脚,看见对面有红色在绿意中晃动闪烁,万绿丛中数点红,这是春天的颜色!那是一片茶园,身穿红衣服的采茶女在茶丛中忙碌。
此时,不知是谁哼起了《采茶曲》:“……左采茶(来)右采茶,双手两眼一齐下,一手先(来)一手后,好比(那)两只公鸡挣米上又下……”轻快悠扬的旋律送我们踏上回家的路。